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如何改变脑转移患者的命运
2025-09-08 16:32
阅读:243
来源:爱爱医
作者:张建鑫
责任编辑:点滴管
[导读] 脑转移瘤是癌症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近20%的癌症患者会经历这一过程[1]。随着全身治疗的进步,患者生存期延长,脑转移的发生率也在上升。传统上,全脑放疗(WBRT)是主要治疗手段,但其对认知功能的长期损害促使医学界寻求更精准的替代方案。
脑转移瘤是癌症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近20%的癌症患者会经历这一过程[1]。随着全身治疗的进步,患者生存期延长,脑转移的发生率也在上升。传统上,全脑放疗(WBRT)是主要治疗手段,但其对认知功能的长期损害促使医学界寻求更精准的替代方案。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因其高精度、低毒性,逐渐成为脑转移治疗的核心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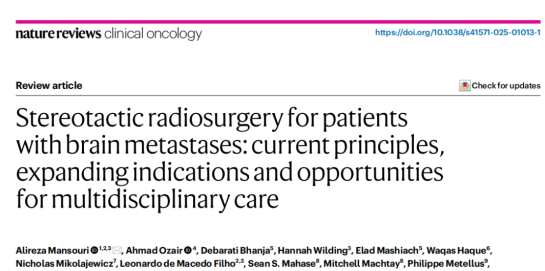
近期,《自然综述·临床肿瘤学》的一篇综述系统梳理了SRS的进展与挑战,揭示了这一领域从“一刀切”到个体化、多学科协作的转型。
SRS的适应症拓展—从寡转移到多发性脑转移
过去,SRS主要用于1-4个脑转移灶(寡转移)的患者。然而,随着影像技术和放疗计划的进步,SRS的适应症逐步扩展。例如,日本的一项大型研究(JLGK0901)表明,即使患者有5-10个转移灶,SRS的生存率和安全性仍与寡转移患者相当[2]。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以病灶数量为标准的治疗模式,转而关注“累积颅内肿瘤体积(CITV)”。简单来说,若多个小病灶的总体积较小,SRS可能比全脑放疗更优,既能控制肿瘤,又能保护认知功能。
对于超过10个转移灶的患者,治疗决策需综合考虑肿瘤生物学特性(如黑色素瘤易多发转移)、系统治疗的颅内渗透能力(如EGFR突变肺癌的靶向药)以及患者整体预后。未来,影像技术的进步(如高分辨率MRI序列)可能进一步优化SRS的精准度,帮助筛选适合局部治疗的患者。
分次SRS—大病灶与关键区域的治疗新策略
传统单次SRS对大于3厘米的病灶存在局限性,高剂量可能增加放射性坏死风险。分次SRS(如3-5次治疗)通过降低单次剂量、提高总生物效应剂量(BED),在控制肿瘤的同时减少副作用。例如,5次30 Gy的方案在多项研究中显示出优于单次18 Gy的局部控制率,且放射性坏死风险更低[3]。此外,分次SRS对邻近脑干、视神经等关键结构的病灶更具优势,因为它允许正常组织在分次间修复。
然而,最佳分次方案仍未统一。目前多项临床试验(如ALLIANCE-071801)正在对比不同分次模式的效果,未来可能需要根据肿瘤类型、体积和位置制定个体化方案。例如,黑色素瘤脑转移可能需要更高剂量,而肾细胞癌因放射抵抗性需平衡剂量与安全性。
多学科协作—手术、放疗与系统治疗的整合
脑转移的治疗不再是单一科室的任务。对于可手术切除的大病灶或引起症状的转移灶,手术联合术后SRS已成为标准。但近年提出的“新辅助SRS”概念颇具潜力:在手术前进行SRS,可能减少术中肿瘤细胞播散至脑膜的风险。回顾性研究显示,新辅助SRS的脑膜转移率显著低于术后SRS(5.8% vs. 16.6%)[4]。此外,术前SRS的靶区更清晰,可减少对正常脑组织的照射,降低放射性坏死风险。
与此同时,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崛起改变了治疗格局。例如,EGFR突变肺癌患者使用奥希替尼可有效控制颅内病灶,部分小病灶甚至无需立即放疗。然而,药物与SRS的联合时机和顺序仍需探索。回顾性研究提示,靶向药与SRS同步使用可能增加放射性坏死风险,而间隔治疗(如SRS后2周再启动靶向药)可能更安全[5]。类似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抗体)与SRS的协同效应备受关注。临床前研究表明,放疗可释放肿瘤抗原,激活免疫应答,而免疫治疗能增强这一效应。但临床实践中,约30%患者出现治疗相关影像学改变(TRICs),需鉴别是免疫激活还是放射性坏死。
挑战与未解之谜
挑战与未解之谜尽管SRS进展显著,多个关键问题仍待解决。首先,放射性坏死与肿瘤复发的鉴别。两者在常规MRI上表现相似,但处理策略截然不同:前者需抗炎或手术,后者需追加治疗。目前,先进影像技术(如氨基酸PET、磁共振波谱)正在临床试验中验证其鉴别能力。例如,氟西洛文PET在初步研究中显示出高敏感性,可能成为未来标准工具。
其次,治疗顺序的优化。例如,BRAF抑制剂与SRS联用可能增加放射性坏死风险,而抗体偶联药物(如T-DM1)与SRS的神经毒性也需警惕。这些发现提示,多学科团队需根据药物特性调整方案,必要时推迟或分阶段治疗。
最后,个体化治疗的实现。基因组学研究正在探索放疗反应的预测标志物。例如,某些基因突变可能与局部控制率相关,未来或能通过分子分型指导剂量选择。此外,人工智能辅助的放疗计划系统可能进一步优化靶区勾画,减少人为误差。
未来展望—从技术革新到以患者为中心
SRS的未来发展将围绕两大方向:一是技术创新,如MRI引导的实时放疗、连接组学(Connectomics)避免关键白质束损伤;二是治疗模式的整合,例如“中枢降期”(CNS downstaging)——通过高效系统治疗缩小病灶,使原本需全脑放疗的患者转为SRS候选。此外,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视将推动更灵活的随访策略,例如利用脑转移速度(BMV)评估复发风险,动态调整治疗强度。
总结
总之,SRS正在重塑脑转移的治疗范式。从精准放疗到多学科协作,从单一局部治疗到与全身治疗的深度融合,这一领域的每一步进展都彰显了医学的个体化与人性化追求。未来,随着更多临床试验数据的积累,SRS有望在延长生存的同时,真正实现“护脑”与“抗癌”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 Ciérvide R, Martí J, López M, Hernando O, Prado A, Alonso L, et al. Single and multitarget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SRS) with single isocenter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brain metastases (BM):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Clinical & translational oncology :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Spanish Oncology Societies and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Mexico. 2025.
2. Harary PM, Hori YS, Annagiri S, Akhavan-Sigari A, Persad ARL, Ustrzynski L, et al.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for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 brain Metastases: Systematic review and Illustrative case present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neuroscience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Neurosurgical Society of Australasia. 2024;130:110927.
3. Lee CC, Chen CW, Yen HK, Lin YP, Lai CY, Wang JL, et al. Comparison of Two Modern Survival Prediction Tools, SORG-MLA and METSSS,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Long-bone Metastases Who Underwent Local Treatment With Surgery Followed by Radiotherapy and With Radiotherapy Alone. 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2024;482(12):2193-208.
4. Ma J, Del Balzo L, Walch H, Khaleel S, Knezevic A, Flynn J, et al. Clinical Outcomes and Targeted Genomic Analysis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Brain Metastases Treated with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 2025;8(2):338-46.
5. Mansouri A, Ozair A, Bhanja D, Wilding H, Mashiach E, Haque W, et al.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current principles, expanding indic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ultidisciplinary care.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2025;22(5):327-47.
版权声明:
本站所注明来源为"爱爱医"的文章,版权归作者与本站共同所有,非经授权不得转载。
本站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
联系zlzs@120.net,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本站所注明来源为"爱爱医"的文章,版权归作者与本站共同所有,非经授权不得转载。
本站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
联系zlzs@120.net,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热点图文
-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如何改变脑转移患者的命运
脑转移瘤是癌症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近20%的癌症患者会经历这一过程[1]...[详细]
-
3D打印与AI辅助技术在泌尿外科临床应用的意义
随着精准医学理念的深入,泌尿外科诊疗正从经验性决策向个体化精准干预转变。3...[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