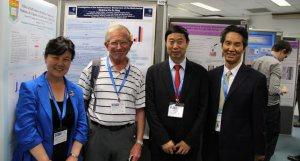一位男医生的“剩女”日记(2)
2011-01-26 09:55
阅读:2130
来源: 申江服务导报
作者:大*勒
责任编辑:大弥勒
[导读] 今天一个妈妈带着女儿来看胃
女儿脉象弦紧,肝郁不舒,久思伤脾。绝对是黄莺莺再世,林妹妹附体。我悲戚地摇了摇头。“剩”是一种病,除了嫁人无药可医。然而我毕竟是医生,死马当活马医是我当医生的本分,也是我救不死扶轻伤的行医要义。我“唰唰唰”提笔留丹青,在病历卡上以潇洒的火星体写下了处方。
我把病历卡谨慎地递到了女儿手里,说:“拿好,趁热。去草药房抓药。有字看不清楚就赶紧上来问,但时间不能隔太长。”女儿嘿嘿笑了笑,我的意思她懂的。她积年忧郁的“剩”被我的冷笑话感染了,她的青春至少在这一刻重又显露,而“剩”则成了被褪去的外壳。
母女俩走的时候,我本想问小MM要***码来着,想想还是忍住了。宁可我恤天下人之剩,不可天下人知我剩。作为病人的精神信仰,我的雕像不能坍塌,作为神医的青年形态,我的剩态必须掩盖。
我被自己“搞七廿三”的思路深深感动,信步来到诊室阳台。窗外,上海下着妖异的雪,忧伤而华丽就像天下所有剩男剩女经历冬天后的再次微笑。只要能够微笑,雪霁就一定能初晴,剩女的冬天就一定能成为往事。
版权声明:
本站所注明来源为"爱爱医"的文章,版权归作者与本站共同所有,非经授权不得转载。
本站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
联系zlzs@120.net,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本站所注明来源为"爱爱医"的文章,版权归作者与本站共同所有,非经授权不得转载。
本站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
联系zlzs@120.net,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